花斑癣会不会传染给别人亲嘴?花与云(3)她喜欢上小弹花匠蒋益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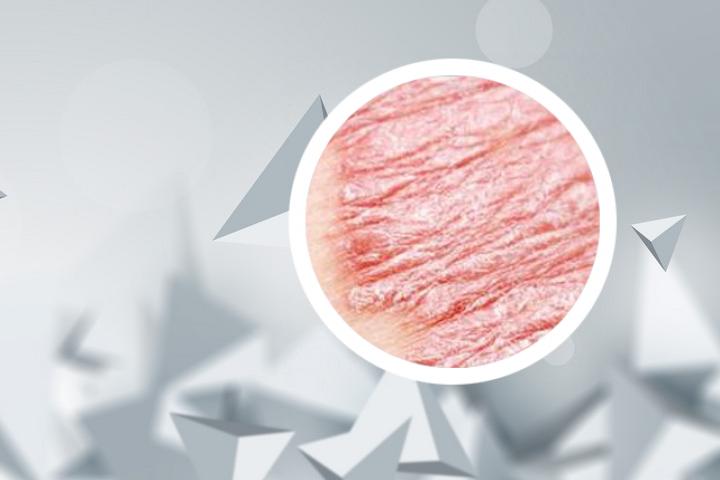
冯海花爱上他,两人分不开了。
“你啥时候带着我走啊?蒋哥,这里并不是我的家。
在这家我简直一天都不想再呆下去了。
我姐夫看人的眼神好可怕。
他平时又不爱和人多话,外人看着老实。
其实他咋想没谁知道,我姐防他就像防贼。
”“他欺负过你吗?”(只是说他的那种眼神。
)“倒没有。
我姐提防着他呢……难保没有个大意的时候。
我经常害怕呆在家里。
”“你尽量,最好小心些!”“已够小心了,觉都不敢睡得太死。
”“你不会跑吗?”(私奔。
或许是真的放不下。
她同样害怕外面,所以才能对小弹花匠的打扰怀疑。
她又患得患失。
他看起来也有些顾虑。
也只能默默地等着他拿个主意。
)“蒋益灵,说句实话,你真的喜欢我吗?感觉到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退路了。
”“那是当然。
”“那你就立马带着我走。
我可以打下手,愿意跟着你和叔叔到处替人弹棉花。
我也不怕风餐露宿,哪怕饱一顿,饿一顿也都不害怕的。
我还可以给你和叔叔洗衣服做饭。
你好像不干脆,等得我毛焦火辣。
”“只是这件事情,得先跟我叔商量好。
”她和蒋益灵在河边的一片小松树林里,有时候是坐在扯了棉花杆,已经犁地准备栽苦油菜的田埂上见面,借着夜幕的掩护,他俩搂抱亲嘴。
有一次被她姐夫张田虎割秀山草回来当场碰到过,为了讨好他闭上嘴,不把事情讲出去,可能闹得四乡八里沸沸扬扬的,更是为了不受他的要挟,进而提出非份要求,冯海花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帮他做双千层底布鞋。
也幸亏她的姐冯雪珠还能够震得住他,姐夫的确有些怕老婆,否则,冯海花可能早逃不脱他纠缠。
这种话她当然不好公开对姐姐说。
“我姐就是那种急性子。
”谁能够料到,张田虎一月后(寒冬腊月)在黑龙滩水库工地上被石头砸死了。
朱荩当年还小,跟着舅舅们上工地,他在那地方玩,是看到他被砸得头破血流的,连脑浆都淌出来了,血流了一地,积在生长着蒲公英和车前草的泥巴路小水坑里,看着黑糊糊的,起了黏稠的一厚层皮。
他还看见了张田虎表哥脚上那双新鞋,就是冯海花秋天替他加班加点赶做出来的那双。
他在参加大会战民工的住地对人吹过牛,当然没有傻到当众说出小弹花匠和张海花的那件事。
布鞋是他小姨子做的,完全不必要怀疑,大家还一直夸她有良心,也不亏得她姐和姐夫心疼。
老天爷会安排,这就是一个人的命,张田虎该得那天早死。
据说当天他请了假的,不出工,倒也不是他想躲奸,是在水库工地附近,大约七华里路有个李家湾,李家湾有一个四十岁不到的寡妇,张田虎给陈七介绍了这个婆娘。
他俩换了身干净衣服,张田虎表哥还特意穿上那双新鞋,兴冲冲地要赶路带人去相亲。
陈七又是他姑家的老表。
这时候负责安全的人都已吹过铁哨子了,纷纷跑开,有的躲了起来,别人没防他俩会突然冲出来。
估计大约可以跑过去,炸响了。
烟尘四起。
事故一共死了两个人,他俩还是亲戚。
路远,最主要是陈七他家并没有什么得力的人,由公社干部作主就把他埋在未来水库附近的山上,叫他看守水库。
他的坟是石头垒成的,轻易不会坍塌,若干年后,水库成了著名的风景区。
当朱荩年迈的时候已经退休了,有一年回老家挂青,听隔壁学校那些去湖边搞烧烤的学生回来说,那地方发现了座烈士墓。
当年没有立块碑。
现在这块巨大石碑是从开发旅游角度考虑后来才立上的。
无中生有。
特别不可思议的是,又有专家考证,游击队在那个山垭口跟敌人遭遇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。
当然朱荩不知道他们嘴上说的是不是陈七。
或者又另有隐情,历史久远,扑朔迷离。
与此同时,冯海花与那个小弹花匠爱情在往更深的层次发展。
她用手帕包来水煮花生,五个带壳煮熟的鸡蛋。
“叔叔不同意带个女人上路,不方便。
”“我不会拖累你们。
我能够给你们帮忙,什么事都会干。
你们刚停下手上的活马上就有热水有饭吃。
衣服更不会有汗斑。
”“说过这些了,叔叔直接摇头。
我了解他心思,手艺人,这不是家乡,怕惹祸。
”“干脆,你去直接向我姐提亲。
她其实更巴不得我能够早点嫁人。
”“可你的姐夫死没多久,才办过丧事。
”“和我又没关系,那是我姐夫。
”好像冯海花也跟着姐一起守寡一样。
“还是等我快回家的时候再说吧。
”“不一块儿走,那我到哪里去找你呢?”他俩其实早都不局限于只是搂搂抱抱,亲亲嘴。
次年,开春的时候,就是有一条狗在油菜花地里让大黄蜂蜇了,有个男人又让疯狗咬伤然后害恐水症死掉,闹得人心惶惶的那些日子。
壮劳力还全部都在黑龙滩水库工地上。
“如果,我是说的如果疯狗窜到我们村里来了怎么办?孩子们来读书的路上提心吊胆。
”学校的董校长上报了公社干部,公社命令民兵组织一支打狗队,终于把疯狗杀死在南酸枣树下。
那些从早到晚害怕的老头老婆婆都松了口气。
娃娃们上学的路上也更叫人放心了。
就在此时冯海花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她肚皮一天比一天大起来,用皮带勒,等到最后眼看再也藏不住了。
弹花匠俩师徒却没来。
听说他俩不在这一带找活干了,又仿佛说,疯狗咬死的人就是蒋益灵。
本来弹花匠怎么说都是个手艺人,在乡下,大多数人也是敬重手艺人的,马上托个媒人来三头对六面,嫁出去,神不知鬼不觉。
冯雪珠气得连煽她妹子冯海花一阵耳光。
“弹花匠是平原上哪个区哪个公社哪个小地方的人,大队有谁知道?”“我不晓得呀,姐,他从来没说。
”“他狡猾,你也不问问。
”“从没问过。
”现在可怎么办,你也真够糊涂的。
“又到哪里找人来负责。
”“我本来以为他走后还会转来接我的。
”“他叫蒋益灵?”光知道名字有屁用。
想私奔?如果当时私奔了倒还好,省去麻烦。
现在张海花脸丢大了,一家人都跟着她出丑,没法再出门见人。
把脸搁在哪儿?姐妹俩从苦李井一个姓庄的卖油郎口中打听到弹花匠家的地址,但也相当模糊,只能是去碰碰运气。
冯雪珠坐客车出门去找老弹花匠,听说那师徒又是叔侄,大家还猜他俩是父子。
家倒是找着了,谁会想得到呢,叫蒋益灵的小伙他在老家是结过婚了的,而且都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。
冯雪珠当面跟对方闹起来,蒋益灵毫不客气说,你回家先问清楚再来闹也不迟,问她肚子里的娃儿到底是我的还是在水库上死的那个姐夫的。
她说等老娘回家挖骨头出来问清楚。
“怪不得他不肯带妹子走呢。
好像他的老婆还来过一趟养鹅寨这边,本意是商量,她打算和蒋益灵离婚,带着儿女走也成,如果冯家这边同意的话,把双胞胎留在蒋家也可以,她心甘情愿腾出位置让他俩结婚,希望能救得下丈夫一命。
当她苦苦地一番思想斗争后,终于拿定主意,不料冯海花却不干。
她宁死都不做这种蠢事,口口声声蒋益灵就不是人,而是畜牲。
他分明知道冯海花跟死无对证的姐夫张田虎到底是怎么回事,故意说出那种话,连死了的人他都不放过,未免歹毒。
“也太伤人了。
”怪就怪蒋益灵缺少了一份男人的担当,他本来该死。
他老婆只后悔自己来得太迟,是个打灯笼火把都难找的好女人,但为了那种男人真不值得。
冯海花本想用包耗子药结束生命,她才十七岁,并且说过这辈子都不会愿谅蒋益灵的。
即使死了,也叫他永远感到内疚。
他俩同样都是傻女人,到这地步还爱着弹花匠。
蒋益灵的老婆哭着走了。
孩子们在身后追着她,外乡女人边离开嚎啕大哭起来。
她一路上带小跑。
事隔多年,已快五十年过去,朱荩还清楚记得起1965年冯海花吃农药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门外(他其实并没有亲眼看到别人抬她,跑隔壁去的时候晚了点)。
人都已经搁在大院坝三合土地上,所有人慌慌张张,忙前忙后,同时进进出出。
冯海花让人灌大粪的情形朱荩一辈子肯定都不会忘。
又闻到了一股浓烈粪臭味,他此时此刻不停地想着,再也不敢偷吃马桑泡了。
她那时候披头散发的,蜷缩成了一团,浑身轻轻打抖,嘴角角吐清水。
她忽然抬下巴偏脖颈凝望天空,一会儿又把脑袋藏在别人夹肢窝。
她脸痛苦得早都扭曲变形。
有双手揪她(抓扯)乌黑的头发。
(好紧张的中午,浑身都是汗啊。
外边太阳有点大。
无聊中,又有人舀粪水啪嗒啪嗒跑来了。
梦里她才活得转来,不要再胡思乱想。
事情已经糟透了,她没有别的路走。
)男孩朱荩相当恐惧,他比地上那个让人灌粪的人还紧张,快透不过气来,把手攒紧,感觉到手掌心全是汗。
大半男男女女背上都是白花花汗斑,有些人额头上挂着汗珠。
有短暂时间,朱荩甚至误以为冯海花姐姐是从房顶上瓦沟栽下来了。
她居然吃得那么多,肚皮胀鼓鼓的。
他抬起头凝望着瓦檐边上,阳光刺痛了眼睛,火辣辣的。
她爬到房顶去干什么呢?掏鸟蛋。
周围空气中散发出一股臭味,谁打了个屁!他害怕闻。